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认为历史是“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是发展变化的。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梁启超是进化论的革命论者,他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连续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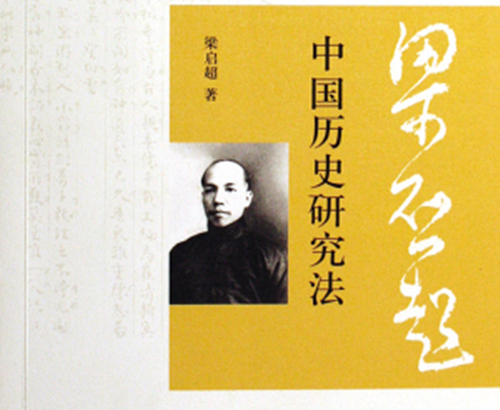
他认为,只有这种连续的人类活动才能构成历史,才是研究对象,而那种在空间上“含孤立性”,在时间上“含偶合性断灭性”的活动,“皆非史的范围”。虽然梁启超的结论绝对了一些,但他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连续过程,比用静止的观点看历史的旧史学家要高明多。
梁启超还强调对因果关系的探讨。他认为研究出的某一历史活动的那个“总成绩”就是“果”,这个“果”必然是另一活动的“因”。
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夫成绩者,今所现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因;而今之成绩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
梁启超在同时也看到了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一因多果,一果数因,除纵向的因果关系外,还有横向的因果关系,同一时代的某一活动和其他活动有因果关系,这一地区的活动和别的地区的活动也有因果关系。
正因梁启超强调历史的总体性、连续性和因果关系,所以他在史著中特别推崇通史,在史家中特别推崇“通人”。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用了很大篇幅来叙述能贯通古今的各种专史的写法。他认为旧史体中只有能反映出事物全貌的纪事本末体为最好,史家则必须成为德、学、识、才皆佳的“通人”。
梁启超很重视历史研究的目的性,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写道:“凡作史总有目的,没有无目的的历史。”
他认为西方史学所鼓吹的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的观念,在中国从来没有。中国史家向以历史为载道的工具,社会在进化,“道”也在变化,因而历史研究的目的不可能凝固不变。旧的史学研究只是为了少数统治者提倡“资鉴”,而现代史著则“为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以达到“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的目的。这就把史学服务对象大大扩展了一步。
梁启超又非常强调史实的客观性。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论及史家四长时,主张以德为首,而“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所谓真实,旧史“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因而夸大、附会、武断都是要不得的。史家应提倡实事求是,对旧史不可轻信,“十之七八应取存疑态度”。
梁启超在论及历史研究的目的性和史实的客观性时,与旧史学家不同的是,他更看到了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并试图从史家的主观方面去找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这与传统的旧史学家相比更要高出一筹。
梁启超在回答谁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时说: “若把几千年来中外历史上活动力量强的人抽去,历史到底还是这样与否,恐怕是问题了。”“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如何?”
然而仅仅看到这一层是不够的,他提出了“历史的人格者”这个概念。所谓的“历史的人格者”,按梁启超的解释,是指在历史中起主动作用而能影响社会的人物。这些“历史的人格者”,其数量古今不同,在“文化愈低度”的时代,这种人愈少,“愈进化则其数量愈大”,“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
故“历史即英雄传的观念,愈古代愈适用,愈近代愈不适用也”。换言之,在古代是英雄创造历史,今后是人民创造历史。此外,梁启超在论及英雄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时势与英雄的关系时,也得出了与传统旧英雄史观不同的结论。
他认为,虽然从现象上看似乎一切史迹皆少数人创作的结果,很少数杰出人物背后却不能没有“多数人的意识”在发生作用。“首出的人格者”和“群众的人格者”是相辅相成的。研究历史的奥秘在于少数的个性何以能扩充成为一个时代一个集团的共性,以及一个时代一个集团的共性何以体现在少数人的个性之中。为此,梁启超特别提出要注重研究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因素,认为这是“史的因果之秘藏”地。
历史是一门实证科学,历史资料的有无和其真实与否是能否得出科学结论的重要因素之一。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梁启超特别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他把史料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字记录的史料,如史部书籍、有关文件、逸书、金石铭文等;另一类是文字记录以外者,如现存实迹、传述口碑、古物等。
但这么多的史料往往散布各处,必须用精密明敏的方法才能搜集到。他特别推崇归纳法,并以大量篇幅介绍它。梁启超还十分重视史料的鉴别,他指出“史料之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与传统史学不同,他对史料的理解十分宽泛,把史料区分成两种12类,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梁启超还提出了具体的搜集史料和鉴别史料的方法,书中列出辨伪公例12条,证明真书方法6条,伪事由来7条,辨伪应采取的态度6条。虽然梁启超的史料学理论和方法还有很多不足,但毕竟跳出了传统旧考据学的框框,使近代史料学得到很大发现。
搜集和鉴别史料固然重要,但“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
所谓“论次之功”,就是撰写历史的方法。在梁启超看来,史事之间相互关联,息息相通,不独一国的历史是整个的,世界的历史也是整个的,这就要求史学家能够提纲挈领,用极巧妙的方法反映出历史事实。要想做到这点,史学家要阐明社会与时代背景,理清事件的眉目,说明事实的因果关系。
当然,由于历史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二者所适用的因果律也有差异,这正是历史难以把握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史学家发挥作用的方向所在。为了使读者学会研究历史的因果关系,他列出程序:先画一“史迹集团”为研究范围,即确立研究范围,然后搜集鉴别史料,注意集团外史事的影响,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中的“人格者”,深入研究史迹中的心理因素和物质因素,并估量二者最大的可能性,寻找事件发生的导火线、原因和结果。
在论述这些程序时,他并列举出大量实例,从而加强了说服力。 《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之后,风行一时,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日本史学家桑原骘藏著《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文,虽然纠正了梁的不少错误,但对于梁的整本书评价较高,由此可见梁启超此书的影响之大了。
在其《补编》写就之前1922年12 月,梁启超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的一次讲座上,他对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进行“修补”,修补的内容主要有三处:
其一,归纳法只适宜整理史料,不适宜研究史学,研究史学要靠直觉;
其二,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而历史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
其三,他认为历史现象中人类平等观念和“文化共业”是进化的,其余则是按照“一治一乱”的方式循环着。由于这三点正是《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精华所在,对它们的“修正”,便意味着对全书基本观点的“修正”,这反映出其历史思想的退步。
-
上一篇: 梁启超的《墨子学案》
-
下一篇: 柳永死后是谁替他安葬



















